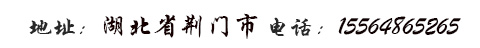我爱的人,是我的爱人
|
白癜风怎么得的 http://pf.39.net/bdfyy/bdfzg/181001/6559327.html 摄影:MOON文子模特:金浩森 1 大厅里昏昏沉沉的,桌椅也凌乱,墙角的空酒箱快堆到了天花板,暗红团花的地毯更加不洁,随处可见香烟烫过的细小窟窿。要不是花台已经搭建了一半,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有一场婚礼要在此举行。 浣辛找不到开关,想叫个服务员来开灯,里里外外跑了一圈也没见半个人影。 这家酒店就像被废弃了似的。 “是这里吗?别走错了。”浣辛望着仪夏。 隔天就要走马上任的新娘自己也很迷糊,环顾左右,半晌才很不确定地点点头:“我们现在面朝的方向不就是西吗?我阿姨说就是这里,西厅。” 浣辛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单纯的陷在甜蜜爱恋中的朋友解释,这和东厅西厅没什么关系。拿一个距离市区半小时车程的破败酒店来嫁女,那个女人也太心急了。嫁出门万事大吉,临了演一出“母慈女孝”的戏,多少落个好名。最后这点表面工夫都懒得做,可是要被人骂的。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新郎和伴郎来了。看他们的脸色,一样很蒙。又过了十来分钟,仪夏的继母领着司仪来了,倒也很客气地赔笑:“让你们等了!顾老师明天有好几个场子,比较忙,今天都在排练。”说着转过头去问那个司仪:“顾老师,那我们现在开始走一下?” “爸爸不来?”仪夏失落极了。 “他被领导喊去开发区陪着参观了。官大一级压死人。” 被称为“顾老师”的司仪顺着花台走到最前面,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人,递上一支话筒。顾老师“喂”了几声也不响,那人接回去拨弄了半天也没修好,转身就走了。浣辛以为他是去找懂的人来调试,结果直到他们撤离,那人也没再回来。 顾老师说:“你们家没什么特别的流程,主要就是父亲送女儿上台,还有改口。爸爸没来,妈妈就代替一下吧,回去记得教一下爸爸。” 没有话筒扩音,顾老师尽量叫得大声,余音回荡之下,一丝喜庆的感觉也无,倒显得很苍凉。 仪夏在继母的陪伴下上了台。顾老师提醒道:“走慢一点,明天穿上婚纱可不能走这么快……新娘右手抬起来,假装抱着捧花……对……” 渐渐走到花台中段,浣辛只听“哐当”一声,仪夏和继母都随着台子陷了进去,像综艺节目里答题失败者遭受到降落的惩罚一样。众人慌忙上来搀扶。浣辛拽着仪夏的胳膊,拽着拽着忽然很气愤,走到一旁打了个电话给她父亲的秘书:“阿乌姐,是我,浣辛……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定个明晚的宴会厅好吧,人不多,大概二十桌左右的……是啊,挺急的……明天是万事大吉,估计结婚、乔迁的一大堆,要是订不到的话你问问迎宾馆,他们一般会留一两个厅给机关单位应急。哎,哎,辛苦你了……这是我私人请你的事,你不要跟我爸说哦……” 大家都听明白了浣辛的意思,刚刚受了惊的仪夏眼里噙着粼粼的眼泪。新郎和伴郎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开口。仪夏的继母拢了拢头发,很小心地问:“你这是……” 浣辛一把搂住仪夏,凛凛而有礼地注视着她的继母:“叔叔没来,有些话请你带给他——他舍得这样嫁女儿,我不舍得这样嫁朋友。仪夏往后的人生都是自己的了,有困难,不会给你们添麻烦;有光,也不想让你们沾。如果念在父女一场的份上,你们还愿意尽点心,就赶紧通知客人,说喜宴换地方了。” 2 狠话放出去,浣辛自己倒也忐忑。好在阿乌很快回电,说雅典国际有一场谢师宴退订了,正巧捡了个漏。但不幸的是,几乎全城所有的婚庆公司当晚都没有档期。 浣辛正犯愁,一个陌生的“明天这种黄道吉日,订单半年前就开始下了。现在除了我家,你不用考虑别人了。” 浣辛驱车前往朱雀门大街,七拐八拐地找到了这家名为“日月于征”的婚礼策划公司。黄昏的光线使得落地窗倒映着密密的楼厦的影子,玻璃上倏忽飞过的鸽群更让她无法看清楚窗子后面那个穿着白衬衫端了咖啡杯一口一口呷着的男人到底是怎样一副面孔。 浣辛下了车,那人迎了出来:“你好啊,东方小姐。” 原来是两个小时前才与他们道别的顾老师。他向浣辛伸出手:“顾佑。顾意的顾,保佑的佑。” 浣辛蜻蜓点水地握了一下:“希望老天保佑,你不会顾意借这个机会狠狠敲我一笔。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那个豆腐渣花台已经是你们的最高水准,那你还是不要耽误我另找他人的时间了。” 顾佑喊冤,说这一切都是新娘母亲的安排——为了省钱,把本来可以一站式服务的项目拆成零散的单元。她只雇了他作为司仪,剩下的事他一概不知。 “她自己找两个民工来搭了个台也不是不可能。” 浣辛扶额:“那不是她妈妈。” “我看也不是。” 浣辛用十分钟时间浏览了画册和视频,迅速定下一套方案。刷完卡,她踏着一地流离的暮色出门去。顾佑送她上车,临走前,她又降下车窗:“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名字和电话的?” “方法太多了。最简单的,可以拍一下你包裹上的快递单。这个世界没有秘密。” 浣辛瞪了他一眼,踩下油门,绝尘而去。 仪夏的婚礼办得很圆满。她父亲向新人寄语时,仪夏还纹丝不动。待到作为伴娘的浣辛捧着婚戒走到她身边时,仪夏整个人哭到不能自已,抱着浣辛泣如筛糠。这大概是全场唯一有些失仪的小插曲了。 散席后,浣辛陪仪夏去了新房,说了一会儿话就回了。到了地下停车场,却见顾佑倚着她的座驾在抽烟。和先前台上西装笔挺衣冠楚楚的样子对比起来,卸下行头的他像一把松弛的弓。 “顾老师,为了区区一万块钱尾款,不至于穷追猛打,半夜三更跑来缠着我吧。” “那倒不是,不过东方小姐你好像不太懂礼数啊。” “怎么讲?” “我忙活了一晚上,除了开场前吃了一块白斩鸡,整个人粒米未进。你连请我吃一顿夜宵的客气话都不说,真的心安理得吗?” 浣辛好气又好笑地看了一眼手表:“这个点,泰国菜和日料就不要想了,只有烧烤。” 凌晨的江风很盛,长桥卧波,灯带逶迤,头顶上,暗寥的云向南方缓缓飘去。浣辛眼看顾佑就着一扎冰啤从荤的吃到素的,再从素的吃到荤的,整个人都蓬松温暖起来,神似一个烘得半熟的甜甜圈。 “东方小姐,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 “顾老师你请讲。”浣辛忍着笑意,像打擂般一招一式工工整整地配合他使用敬语。 “你为什么姓东方啊。” “我爸就姓东方。” “哦,那我给你唱首歌吧。” “要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那就算了,这招很多人都用过。” “你怎么这样啊。你拆了我的台,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就你这应变能力,还当司仪?把剩下的几个扇贝吃完了赶紧回去提高一下业务素质吧。” “不,不行。我要唱歌。”顾佑像座斜塔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到一旁的小型舞台上,往高脚凳上一坐,手指在点歌机上滑来滑去找曲子。最后到底还是选了一首罗大佑的歌——《恋曲》。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他的声线,在主持典礼时很明亮清朗,换了唱歌,就宽厚喑哑一些,十分接近原唱,像一炉膛朦胧明灭的微热余烬。歌声在宽阔浩荡的江滨摇荡,细小的霓虹灯在远方闪烁,仿佛银河里失群的孤星。浣辛把头歪向有风的一侧,拨弄着耳边的碎发,想起了许多遥远而温柔的往事。 一曲唱毕,顾佑在零散几位食客的掌声中下了台。 “唱得不错。婚礼上怎么不唱?” “我不是卖唱的,也不是谁都可以随随便便听我唱歌的。” 浣辛撇撇嘴:“你不会是因为喜欢罗大佑,给自己改了个艺名吧。” 顾佑专注地看着她。浣辛觉得周遭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庄严。 “怎么了?”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改名叫顾浣辛啊。” 3 浣辛开始害怕听到手机铃声,总担心是顾佑打来的。只是手机长久不响,她又寂寞,拿过来放在手中百无聊赖地把玩。阳台上的一缸铜钱草长得飞快,没几天就长到了膝盖那么高,把洁白的瓷砖都映绿了。她的心倒还是在冗长的光阴里久久地煎熬着。 她这样的人,从容貌到门第,都是别人艳羡或嫉恨的。做学生的时候,行走在校园里,无论男女,从她身边走过都会传来她司空见惯的窃窃私语。那时候的辅导员很喜欢她,说:“当面夸一个人总有恭维的成分,只有夸东方浣辛长得漂亮,才让我觉得是实实在在平心静气的评价。” 浣辛也总是会想起毕业晚会,那么辉煌的典礼,因为肤如凝脂的她登台献舞一曲,看起来倒像是她一个人的谢幕式。观众席上,闪光灯和所有切慕的眼睛汇成星海。身处万人中央,她早就习以为常。 然而,如今就有这样一个人,在她认为即将高潮迭起之时,静悄悄地息了鼓声,又骤然退出。她平生所受到的全部礼遇,加在一起也不能消弭此时所受到的亏待。 仪夏听说后,安慰她,说真正高级的珠宝陈列在玻璃橱窗下,总是浏览的人多,敢据为己有的人少。不是不爱,只是觉得自己不配。 “他也许是在你的光芒下自卑呢。” 浣辛道:“他可不自卑,他是过度自信。这个浑蛋。” 仪夏窃笑:“浑蛋怎么了,就有人为浑蛋埋单呢。” 一天午后,表姐燕呢来了。一推开她闺房的门,燕呢就拿出一件天青色的雪纺荷叶边及膝短裙。浣辛知道她的意思,只是合上书,慵懒地蜷在藤吊篮里假寐。 “你不要在这里装死。别人结婚,请你去做伴娘,你二话都不说。现在我请你,你就拿乔。你当我不知道呢,前一阵子,你朋友在雅典国际的酒宴全是你帮着打点的。你小心我告诉姑姑去,让她铰了你的毛!” 浣辛只得来试衣裳。女孩们在落地镜前摆弄着,燕呢拎了拎裙子的腰身,发觉大了:“你的三围是姑姑给的啊。怎么不对?”浣辛说:“宽松便宽松些吧,只是伴娘,又不是新娘。” 燕呢道:“我就怕你说这样的话。你和姑姑的衣服不都是在湖光大街的那家定制的吗?我特意去的那家呢。我看是你瘦了吧。” 浣辛转头朝镜中看了看,似乎是清减了一些。 “别人夏天都发胖,你是怎么了?”燕呢见她不理,又道,“瘦了无非三种情况。运动,节食,害相思。”浣辛不想因此想起顾佑,但想到的终究还是他,心里不禁恨恨的,也不知是恨顾佑,还是恨自己不争气。她又想到了燕呢的婚礼,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问道:“你婚庆公司请的哪家?” “Loving啊,他们家有一种紫藤拱顶,特别好看。” 浣辛心里念着谢天谢地。她隐隐有种确认,顾佑就是故意吊着她的。她求菩萨保佑不要再看到他,等到了婚礼当天,浣辛看见顾佑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地朝她走来,下意识就拿胳膊肘捅了燕呢一下:“不是Loving的吗?这司仪哪儿来的?” 燕呢似也气不打一处来,说原先那位司仪刚从墨尔本度假回来,吃了澳洲龙虾过敏,现在整个人红得就像只龙虾,迫不得已才请业界的朋友来救场。燕呢的婚宴设在潋月湖畔,顾佑玉立在初秋时节恬淡的山水间,在燕呢那个倭瓜老公的反衬之下,很有喧宾夺主的意味:“好久不见啊东方小姐。” 没等浣辛呛他,燕呢倒先下一城:“怎么,认识?那得了,顾老师今天的出场费就打八折了啊。”说罢拖上浣辛到花园入口迎宾去了。 筵席上,顾佑几次徜徉到浣辛跟前,浣辛都假装敬酒避开了。待到午宴结束,浣辛刚把车开出停车场,顾佑就从边上蹿出来拦车。浣辛一个急刹,伸出头来狠狠地怪道:“你疯了吗?” “你今天害我破财,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假如你说的是八折的事,放心,那两折我来付。但请你不要以这个为理由让我请你吃饭。头一次叫出奇制胜,再一次就是黔驴技穷了。” “我这么说了吗?” “那你要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说。”话音未落,顾佑的头就伸进车窗,一下子吻住了浣辛。 惊慌之中,浣辛的手接连按到了方向盘,车笛骤然响了几声。门口的保安被惊动,又看见顾佑的举动,以为车厢里的女孩受到了非礼,一溜小跑向他们奔来。顾佑还是不肯松口,同时含糊地嘱咐浣辛:“要是他把我当色狼抓走了,拘留的这几天你记得给我送饭。”故而等保安揪住顾佑的衣领时,浣辛只得奋力说了声:“这是我男朋友。” 4 浣辛基本能够猜到,这个人一定是相信情场如战场,才玩“欲擒故纵”这一套。后来顾佑请她去山里吃野味当赔罪,她气性没下去,凭他三请四邀也不答复,只是在“到底是做生意的,眼睛里只认得钱。仪夏婚礼的账一结完,有些人就跟死了一样。” 顾佑不傻,问她是不是怪他前阵子没有联络她。浣辛不吭声。 “我不是故意的,但我也不能告诉你。这是个秘密。” 浣辛不屑:“我早晚会知道。是你说的——这个世界没有秘密。” 她怨他,却又记挂着他。逢上有谁要结婚的消息,她就凑上去帮忙打广告:“‘日月于征’有个叫顾佑的司仪,谈吐啊、台风啊、气氛把控能力啊,都是一流的。” 换了别人,大抵人家要疑心他们的关系。浣辛倒没沾上什么嫌疑——圣裕集团掌门人的千金,未来不是找高干子弟,也总是要与名门巨贾联姻的。真要恋上一个婚礼司仪,那肯定也只是一时兴起。不过她既然开了这个口,面子总是要给的,何况司仪请谁都是请,索性做个顺水人情。 这场婚礼的客人有些鱼龙混杂,浣辛从他们跷二郎腿的姿势和吸烟时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听新娘葳葳说,新郎的堂兄来路不清爽,锃光瓦亮的脑袋不是英年早秃,是从里面出来后就一直习惯剃光。“我劝他少和他们来往,他说往后带着带着疏远,婚礼这么大的事,不请反倒容易惹是生非。” 伴娘团一共五人,葳葳请浣辛领衔。浣辛怕出风头,婉言谢绝了,便由另一个高挑美貌的女孩出任。葳葳叫她美玲。 开席前,浣辛的头发散下来一绺,跟妆师也不知去了哪里。浣辛只得自己去化妆间找发夹。一推门,她就见顾佑赤裸着上身,手中提着刚脱下来的衬衫,经年累月锻炼的好身材展露无余。 “你不是换好了衣服来的吗?”浣辛低着头到妆台上摸索着找那种小黑发夹。 “没发现我和新娘父亲撞衫了吗?” “你以为别人没事就会观察你吗?” “别人我不知道,至少你是。” 婚礼按部就班地进行到了新郎新娘合卺交杯的环节,浣辛正打算陪新娘下去更衣,台下蓦地上来一个光头的花臂大汉,正把一束玫瑰拆散,一枝一枝地握在手中:“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考验过了新娘子的酒量,现在要考验肚量了。”说着拉过伴娘团中为首的美玲,将玫瑰一支支地插在了她的发间、手里、腋下,甚至是胸前。 “现在请新郎用嘴巴把这些花叼起来,再扎成一束,送给新娘。”台上人的脸皆有些变色,美玲更是惊慌失措,只是碍于场面,不好推打抗拒。而座下众客,尤其是喝了酒的男宾,见此情形,纷纷鼓掌喝彩,情状一时难以控制。 新郎为难地看了看堂兄,又看了看无奈的新娘,只得向着瑟缩的伴娘俯下身去。可还没等他闻到玫瑰的香气,全场的灯一下子都灭了。黑暗之中,宾客喧哗躁动起来。趁着慌乱,浣辛一把拉住美玲逃离了现场。 一分钟后,灯火光明如初。新郎举起一捧玫瑰送上,新娘微笑着收下。那光头见此形容,也无计可施,只得悻悻下了台。 婚礼一结束,浣辛就挡住了顾佑的去路:“手和脑子都很快嘛,拉电闸这种事也想得出来。”顾佑像是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一脸正经地说:“看不惯这种拿女人开玩笑的婚闹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新郎要弯下腰用嘴巴叼花的样子让我想到了我哥。” 他说,曾有人将一大包葵花籽撒在地上,让他哥哥跪下来用嘴巴衔葵花籽,并把它们全部嗑完。 5 顾佑又玩起了失踪,甚至到了浣辛打电话、发短信都不接也不回的地步。浣辛到贵德买衣服时途经朱雀门大街,一时没忍住就掉头开到了顾佑的店门口。茂盛的绿植,香水百合浓郁的气味,大大小小的玻璃水培皿……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间铺子已化身一家花店。浣辛将信将疑地对比了一下外围的环境,确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 “您好,买点什么?有新到的多肉和茶花,进来看看吗?” “麻烦打听一下,这里原来有一家婚庆公司……” “是说‘日月于征’啊?就是我这里。他们不做了,房子转租给我了。” “不做了?为什么?” “这我也不太清楚。附近有的人说,好像是欠了挺大一笔高利贷,也有人说他们得罪了江湖上的势力。” 浣辛飞快地上了车,来到圣裕大厦。 阿乌裹着一步裙,足踏恨天高,正“嘚嘚”有声地走在走廊上。见她直奔董事长办公室,忙上前道:“他不在,你有事?” 她父亲的司机明明就在一楼和保安胡侃吹牛,浣辛没理会,箭步上前破门而入。 两鬓微白的东方启摘下读报专用的老花镜,肃然望着这颗掌上明珠:“你下次要是再这样没有规矩,我让阿乌取缔你的指纹。那你有什么事,就只能跟其他预约一样,在楼下候着了。” 阿乌屏退后,浣辛埋怨起来,说全世界都开始不接她的电话。东方启说先前在开会,又问还有谁冷落了她。浣辛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遂请他父亲帮忙找人:“他叫顾佑,顾意的顾,保佑的佑。我不管你走哪一路,白的也好,黑的也罢,你赶紧帮我找到他。” “这是个什么人?” 浣辛低下头捻揉着手指:“他……他欠了我一点钱。” 东方启失笑道:“阿乌前些天才把你的流水打印给我看,并没有多少用度。这人又能欠你几个钱?十万八万的就算了,真要托人找他,还不够四处打点的,你就当买个‘交友不慎’的教训。” “我还有其他事要找他。” 东方启点点头:“回头我让人去处理。” “不要回头回头的,马上!”浣辛拎上包打算回家,走到门口被他父亲叫住:“这个星期太忙,我一直没跟你说。上周在曼谷,你秦叔叔正式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只说看孩子自己的缘分。现在问问你的想法,你看秦冠朗怎么样?” 浣辛没有回头:“我跟你说过一万次我的想法了。如果我没有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惜我们谁都不能忘掉对方穿开裆裤的样子。” 东方启的意思是,两家乃世交,硬生生驳回去有伤和气,让浣辛不妨出国念一阵子书,好慢慢淡化此事。 浣辛恋家,不大想出国,本没有答应。未想后来的几日,秦冠朗接连发短信来约她,浣辛只得开始联系旅居加拿大的朋友咨询就读事宜。手忙脚乱之中,让她更为心焦的是——直到去多伦多的前一天,她父亲还是没能探听到顾佑的消息。浣辛思前想后,念及花店老板所说的“得罪了江湖上的势力”,便致电葳葳,请她丈夫出面,托那个光头堂兄在道上打听打听。 在多伦多,浣辛租住的公寓接近郊区,夜晚十分宁静。这天深夜,她被电话惊醒,听筒那头传来非常嘈杂的市井之声。国内时间是正午,葳葳是在一个卖场里给她打的电话。 “浣辛,有顾老师的下落了。” 6 子夜时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于暗处荧荧亮着。打开葳葳的邮件,浣辛下载了那个视频。视频中,一个男人拆开一包瓜子,“呼啦”一声尽数抛撒到地上:“顾佑你听着,你哥哥三次一共借了二十九万,利息算起来大概一万多。现在啊,我们头儿发了话,说利息一分不要,只要把本钱还上就行。这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你别急,还有更划算的呢。喏,地上这包瓜子,只要你哥跪着用嘴捡起来,把它们嗑完,这账啊,就一笔勾销。不然呢?一周之内还不上钱,就别怪兄弟们不客气了……行,你们靠边站,来个人,把摄像机对准他,我录了好回去交差。” 个头比顾佑矮小一些的男子二话不说便跪了下去,疯狂地舔着地面嗑起了瓜子。一旁的顾佑冲上去将他拉起来,对着镜头承诺:“这个星期之内,我连本带利如数奉还,绝不拖欠。请相信我,东方先生……” 没等顾佑说完,浣辛就“啪”地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据葳葳了解,顾佑头一次“失踪”的那一周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辗转在各种婚礼和开业庆典上,而第二次真正的失踪是因为脊椎和腿骨严重受伤,医院可以查到长达两个月的住院记录。 “利用顾佑他哥好赌的恶习请君入瓮,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在布局操作,浣辛,恐怕你看完视频也就能猜出一二了。” 隔天直达的机票已经售完,别无他法,浣辛只能选择从北京转机。前前后后奔波了近二十个小时后,她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父亲索要她当初的手机。 “手机?在阿乌那里,你放心,你国内的所有事情她都帮你处理了。所有联系你的人,她都一一给了他们你国外的号码。她办事一向很周到,你还不放心?” 接近凌晨,东方启很疲倦,让浣辛早点去休息。浣辛身处颠倒的时差中,脑子像被真空包装一样,却坚持双目如炬地盯着他的父亲。东方启在这种逼人的眼神中清醒了过来,鹰隼般的老眸绷紧后,眼周的皱纹登时密集如织。 浣辛颤巍巍地走到他面前:“顾佑打来的时候你们怎么说的?是说我已经结婚了,让他不要再骚扰我?还是想故技重施,拿他的人身安全和他哥哥的烂账来恐吓他、威胁他?又或者干脆就对他说打错电话了?” 东方启并不惊讶,只是轻轻说了一声:“你知道了?” “这个世界没有秘密。” 东方启点点头:“既然你知道了,那也就不用我再告诉你了。早点休息吧。” “为什么?” “为什么?你心里难道没有答案吗?” “我没有!”浣辛提高了分贝,连带着心脏搏动的振幅也大了起来。 “东方家不可能要一个跑江湖卖艺的女婿。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别想见到那个小子,趁早死了这条心。你替朋友当出头鸟也好,你大手大脚地用钱也罢,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你的爱情,你一生的幸福,我不能不管。” 浣辛觉得很滑稽,大笑起来:“董事长大人,别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了。你懂什么叫爱情吗?妈妈查遍食谱在家花两个小时文火慢炖为你煮一份八珍汤,这才是爱情。她是想你能从一而终像以前那样爱她,而不是为了把你补得身强力壮好去和阿乌共度良宵的。你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以为我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还少吗?” 东方启反手给了她一记耳光。浣辛捂着脸倔强地回过头来望着盛怒之下的父亲:“他再穷,再寒酸,赚的每一分钱都有光明正大的来路。就凭这一点,你这辈子都比不上他。” 7 圣裕走私案最早是在民间悄悄有所传闻,彼时东方启虽已数日未曾露面,但集团运转如常,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说法。直至立夏这一天早晨,CBD所有人都听到了嘹亮的警笛,封条很快像挽联一般森冷凄厉地贴向了这幢在商界屹立了许多年的华厦,连带着那玻璃幕墙所反射的万丈阳光都忽地暗淡了下去。 东方太太一病不起。失火的后院里,从头到尾都是浣辛在配合着公检法前来调查取证的各路人马。她的账户里只剩下三万多块钱,是她以前的工作积蓄,另有五千外币,是学校发放的奖学金。 东方家族和圣裕集团树倒猢狲散,只有浣辛一人处之泰然。昔日的亲眷朋友人人自危,避之不急,浣辛在离开这个生她、养她并给了她爱情的城市之前,却接到了仪夏的电话。仪夏约她去吃烧烤,为她饯行。 江风阵阵的夏夜,星斗漫天,恍如昨日。闪烁的霓虹灯光中,倚筑而歌的却不是故人。浣辛喝着他喝过的冰啤,以前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喝这种廉价的酒,但她越喝越觉得心里亮堂,好像醉倒醒来就能与他重逢一样。 仪夏搂着她:“你这样做,值得吗?” 浣辛双目迷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浣辛,没有人比我更懂你了。你父亲行事缜密,不是绝对亲近的人,怎么可能拿到最有力的证据,使得东窗事发?为了爱情,为了脱离他的摆布,你大义灭亲,亲手把他送进了监狱,不是吗?” 浣辛怔了怔,惘然一笑:“我可没有你说的这么自私和伟大。” 仪夏打开包,掏出一张银行卡推到浣辛面前。浣辛哭笑不得:“我还没有那么穷。” 仪夏说:“这本来就是你的钱啊。你帮我办婚礼的钱我一直存着,现在只是物归原主而已。你猜密码是我的生日还是你的生日?” 浣辛一下子扑到仪夏怀中泪流满面,像是当年婚礼上的仪夏扑到她身上哭泣一样。 8 浣辛后来去了很多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她做过翻译、老师、导游、HR……许多职业。万水千山的行程里,她还是会习惯性地抓住一切有可能的机会去寻找顾佑的踪迹。 这一年暮春,她在成都。同事之中与她最要好的是来自台湾的客家姑娘阿沐。阿沐的男朋友身量不够高大,但笑容很阳光。阿沐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穿高跟鞋,他们打算在夏天举行婚礼。浣辛想,换作以前,她大概又要介绍顾佑担任他们的司仪了。 五月,罗大佑的巡回演唱会开到了成都,阿沐送了浣辛一张票。浣辛问她为什么不和男朋友一起去看。阿沐说只有这一张,一票难求,她又不甘心把钱让那些可恶的黄牛赚了去:“没事啊,作为苗栗老乡,还怕以后没机会听他唱歌吗?” 演唱会上,这个华语乐坛教父级人物从艺四十年来所创作的时代金曲一一被唱响。浣辛的位子不算近,但她也很明显地察觉出这陪伴无数人度过漫长青春岁月的长者正逐渐老去,有些高音已力不从心。她不知道一别十年光景,那个喜欢罗大佑的人现在是什么样子。《恋曲》的前奏响起时,她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环视满场黑压压的人影。 那些伴着旋律摇晃着手机电筒的人,是不是他呢? 台风过境后的八月,阿沐的婚礼先后在苗栗和成都举行。阿沐邀请浣辛当伴娘,浣辛不好意思地说:“客家的婚俗我不太懂,怕出岔子。而且我年纪比你大,还没嫁出去,好丢人啊,哈哈,还是不要了。”阿沐便没有再勉强,找来了发小陪伴。 阿沐家的祖宅位于一个坐山面水的小镇上,风光秀丽,民风淳朴。阿沐的嫁衣、妆奁、喜器都是她的祖母按着客家传统精心准备的,流水席一直从白天吃到晚上。明月高挂,醉颜纷哗,浣辛正在挑选回成都的航班机票,只听阿沐的父亲笑道:“来迟的人赶紧自罚三杯。”浣辛顺着话音向门口看去,一个身着白衬衫的男子径直往娘家的主桌赔礼去了。 他看起来变化不大,还是以前那种清健有趣的样子。但她端着酒杯一步步向他靠近时,却分明看到他的眼神趋于沧桑。他们都不是很惊诧,好像在距故土千里之遥的岛屿上再度相见只是理所当然的事。可他微微颤抖的手,和她灼灼的泪光,还是震动了这克制之中的宁静局面。他先开了口:“你……这次没做伴娘啊。” “你不也没当司仪吗?”她唯有这么说。 席上人多,他们出了门,一直走到深蓝色的湖泊边。远处是暗青色的山,山巅是淡白的云与银色的月。确定周遭再无别人,两人一下子拥抱在了一起。浣辛失声痛哭,并对着湖面大声地喊着:“啊——啊——啊——”十年的郁结在水面上悠悠回荡,旋入夜空。 正如浣辛猜测的那样,顾佑康复后去找她,被阿乌以种种理由拒之门外。后来他朋友的朋友又托了好几个朋友查到了她的出境记录。 “你在国内,或许我还有办法。但跨过太平洋去满世界地找一个人,我的能力还是太微不足道了。”从头到尾,顾佑都没有提到她父亲半个字,浣辛懂得,他从小和兄长相依为命,看重亲情,他不想她为此与父亲生出龃龉。因此,当他说起在新闻上看到圣裕一案时,浣辛也只以“都是过去式了”一笔带过,而不让他知晓,这是她为爱付出的毁灭性代价。说自私也好,说伟大也罢,只在人的一念之间。 不知名的水鸟正在湖心的月影里飞过,夏夜南来的微风含着草木的清香,还在叫着的是蝉与蛙,消失又再现的是茫茫的年华。他们并肩坐在湖边,内心有千言万语,到嘴边却只剩下寥寥数句。他们不知道这是歌里唱的——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还是诗里说的——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次日,浣辛与顾佑一起回台北。她翻下副驾驶座前方的遮光板,对着镜子整理头发时,发现那夹层里有一张照片,是她在毕业晚会上登台献舞时的演出照。 “这个古董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浣辛问。 “是我拍的啊。好了,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秘密了。”他说那时候人人都劝他,这个姑娘复姓东方,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倘若他主动写一封情书给她,怀揣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可能他们之间的相识不会一直拖到仪夏的婚礼。 入秋后,作为浣辛的亲朋好友,仪夏、燕呢、葳葳、阿沐次第收到了一张请柬。请柬制作得很朴素,但封面上的一句话使得她们不约而同地喜极成泣—— 当了那么久的司仪,他终于可以主持自己的婚礼。 做了那么多次伴娘,她终于走进属于自己的殿堂。 丨原文《日月于征》 丨载于年9月爱格B版 推荐阅读 购买指路:淘宝中南天使图书专营店 往期文章 点分享点收藏点点赞点在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oxigechenga.com/mxgcly/8708.html
- 上一篇文章: 荣耀之旅年住棚节以色列深度十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