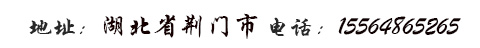新冠加时赛我如何逃离三亚北京和纽约
|
我国著名白癜风研究专家 https://m-mip.39.net/nk/mip_5941808.html站在星星的残骸上观望。 我和M的出门装备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那么这部名为《新冠加时赛》的电影的开端,大约是这样的:时间3月8日,地点墨西哥尤可坦大区。空中正刮着飓风,云朵和棕榈叶撕来扯去,细长的公路正覆盖在乌云下,散发着迷人的银色光芒。一辆租来的尼桑白色小轿车在路边停下,走出一个戴着墨镜的亚洲女人,我,和一个戴着墨镜的美国男人,我的先生M。我们匆匆从后备箱中取出防晒长手套,套在M脆弱的白皮肤的手上。六千六百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击中地球,能量相当于一百万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十多年间地球被灰尘、颗粒、酸雨所笼罩,导致了几乎全部生物的灭亡,其中包括恐龙。这颗行星的降落点,就是尤可坦东部的Chicxulub。镜头一转,回到我和M在纽约东村的公寓中。前两天的早晨6点,我们坐在窗前喝咖啡。M的两只眼袋重得像骆驼的肚皮。昨夜他又一夜无眠。终于,他开口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立刻离开纽约。”他问我想去哪里。我的脑海里迸出一个词:墨西哥尤可坦。那片本应是大海的陆地,总让我感到宁静与稳定。我们所在的纽约曼哈顿下东区镜头再度切回今年开年,我单独回国,和家人在海南过年。我的父亲是只典型的候鸟,北京只要冷意稍显,他就挥翅飞向海南。而且我的父母和所有80后的父母一样,经历过大风大浪,闻得出暴风雨之前的腥味。还记得1月初的一天,听到爸爸妈妈非常严肃地讨论:这次糟糕了!我当时不以为然,认为是他们医疗系统小圈子的谣言。爸爸非常紧张,迅速去药房买了几袋一次性口罩。很快情况直转而下,作为全国人民后花园的三亚亦如临大敌,小区中盛传有从武汉“逃”来的家庭,并有一辆武汉车牌的车子在海边扎帐篷。散步时,亲耳听到一名东北汉子大声对着“那人绝对是从武汉跑来的,我已经报警了……”除夕期间,一起过年的亲戚中有一位忽然开始发烧,全家人如临大敌,把这位洗澡受了凉的倒霉亲戚在地下室关了整整一周。1月27日清晨醒来时,我被手机上十几个未接电话吓了一跳。都是M从美国打来的,大意是已经把我原定1月31日回纽约的机票退掉,买了当天晚上的航班。“立刻回来,否则就回不来了!”我能感受到他每一个句子后面都跟着5个感叹号。比他更积极的是我的父母。他们不但异常赞成女儿临阵逃脱、抛弃亲友,并飞速地安排我乘坐第一趟航班回北京取行李。在父母的心中,儿女的安全永远高于自己。而我呢?抱歉,你还丝毫不了解我,我是个从小就梦想流浪啊、逃亡啊、冒险啊的傻子,我看到父母隔离条件优越,便放心地大吃了一顿,戴着2层口罩,由三亚飞向北京。当天夜里11点,我从北京T3飞向德国法兰克福,只背了一个双肩包,里面是证件和20只一次性口罩。幸运的是,航班竟然空空荡荡,同排的一位大姐看上去非常焦虑,越过两个座位和我搭话,她怕我听不清楚,特地扯下口罩。十多个小时后,落地法兰克福机场。出舱门,我们一群戴着白口罩的浩浩荡荡的中国人安静地涌入通道,只听见焦急的脚步声。一名高大肥硕的德国地勤人员站在通道尽头,胸前戴着牌子,脸上没有口罩。他迎着我们这一批来势汹汹的口罩大军,眼神慌张,估计是被吓得不知是查是躲。法兰克福机场的大屏幕滚动播放着中国疫情新闻,然而无论是机场工作人员,或者候机的人,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包括中国人。我发现同班飞机的乘客们一旦彼此分散,便迅速摘下口罩,这里面也包括从北京飞来的几个外国人。我没有摘口罩,买了咖啡喝面包,躲在一个角落吃饭。我不摘口罩的原因,主要是数名英国人在肆无忌惮地咳嗽。从法兰克福飞回纽约的航班上,便几乎没有人戴口罩了。落地后,我只用了20秒钟便通过电子识别系统进入纽约,没人测量体温,没人询问。二十几个小时后,我终于摘下了口罩。回到纽约后地第二天,我便开始到处走动。去做丝网印刷,做蚀刻画。第三天,我还开始了瑜伽培训和教课。瑜伽工作室的熟人们见到我,纷纷冲上来拥抱,问候中国的疫情,表达哀伤。一方面,她们用善意温暖着我,但另一方面,她们也惊醒了我。我突然意识到:第一,没有隔离就出来混的我是个混蛋,为什么我相信自己完美地躲避了所有可能感染的情况?第二,美国人民tooyoungtoonaive。第三,纽约充斥着我这样的混蛋和迷之自信的市民。我得出结论:纽约一定会完蛋。我迅速地暂停上课(但丝网印和蚀刻还坚持了几次),并迅速和M陷入家庭内战。我的先生虽是美国人,但会说中文,热爱东北炖菜、火锅、大盘鸡。他过去是一名医生,现在在常春藤大学的研究机构工作。他和所有2月初的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口径一致:新冠和流感杀伤力相差不大。同时,他也认为外科口罩作用不大,他的一名医生朋友甚至号称胆敢不戴口罩去中国支援,让我哭笑不得。我和住在加州的旅行作家朋友毛豆子在朋友圈发起小规模募集,为河南和湖北的医生搜刮物资,几小时内就收到2千美元善款。无论海外华人还是国内的朋友,都争着想出一份力。豆子甚至通过土耳其的朋友采购到几百个N95口罩,连夜人肉到我北医三院的发小手中。但是同时,我也对豆子说:咱们中国人现在把货都卷回国,后面全世界暴发的时候就惨了。其实华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无法看着我们的医生裸奔。在我和M不断地争论、我的朋友和家人不停地语音恐吓之下,一周后,害怕冲突的M妥协了,同意躲起来。于是我仅仅在纽约待了10天,便飞去了哥斯达黎加,在南部的热带雨林中整整躲了十几天。我们住在自然保护区的小屋中,每天与猴子、鹦鹉、蜘蛛、食蚁兽为伍。那个保护区几近与世隔绝,一个电网维护小队在附近工作,一半时间修电缆,一半时间在海上抓鱼,他们用鱼交换我们的啤酒。没有人问过任何关于新冠病毒的问题。这样愉快的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只好在2月底再次回到纽约。这次回到纽约,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室内口罩,消毒液已经全部售空。所有华人以及有华人朋友的外国人都颇为紧张,但绝大部分纽约人仍歌舞升平,party连天。密闭空间里人们一边咳嗽,一边拥抱。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囤物资,我列了一份单子,发给我的朋友们,罐头、冷冻食品、面……是的,美国这个农业大国的确不可能缺粮,但有粮和能不能到你手上是两回事,我坚决选择不相信特朗普政府。来到墨西哥的M全副武装去超市这时M和他的同事们已不再乐观,但依旧不认为需要隔离,这让我极为震撼,要知道这时已经是3月初了。这些民主象牙塔里的自由主义小白脸,坚信中国数据不准确,坚信没有明确的证据需要引起大规模恐慌。我问他:那位去见钟南山的利普金教授,不知道回来有没有戴口罩?他回答:听说戴手套了。我听了下巴都吓掉了。如果下巴能掉,这些日子以来我的下巴早为周围不听劝告的美国朋友们掉光了。公共卫生专家们都如此轻怠,就不用提可爱的美国群众了,我再次深深地为这个国家感到遗憾和绝望。为了不让我疯掉,M把大部分工作改成线上,并配合我消毒。但是在禁足了3天后,一天晚上他竟然忍不住偷偷溜出去喝酒,让我震怒。等他回来后,我和蔼地通知他:“你健壮如牦牛,感染了八成也没有事,但我这种有基础病的人,感染就是死。死呢,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可以转世成金刚鹦鹉。但是,请你负责去和我妈说,她女儿是因为你溜出去喝酒传染死掉的。”这一次,M终于被惊醒了。他怕我妈,胜过怕这世界上任何一种病毒。紧接着,他被参与新冠数据模型的制作,研究人员得到越来越准确的来自意大利、韩国等国的数据,形势愈发紧张。3月6日的早晨,他看着每天都要用哮喘喷雾的我,终于同意出逃。到达墨西哥的第二天,M所在的大学宣布全面停课,工作完全转到线上。纽约开始大规模检测,每日确诊数字飙升。我们当初的物资还有几箱口罩滞留在意大利,国内已逾风平浪静,便医院。而当初帮助我们的土耳其也沦陷了,我们再次发动了小范围募集,医院捐赠了一批物资。转眼之间,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oxigechenga.com/mxgctq/6614.html
- 上一篇文章: 本周十大看点墨西哥amp吉隆坡站
- 下一篇文章: 一周新店和纽约一样潮的墨西哥菜,阿拉